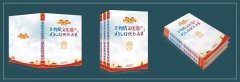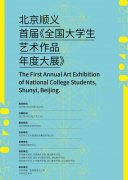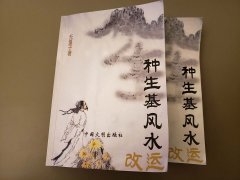|
|
研讨会上展示“世遗”南音 |
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洛阳古桥仍在,南音梨园犹闻。但梨园戏著名剧目《陈三五娘》的明代刊本《荔镜记》,现只存于日本、英国,成为泉州“涨海声中万国商”的一例往事。12月2日至4日,古城汇聚了来自海峡两岸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专家学者,就“一带一路”文化遗产的保护、创新、发展展开讨论。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贾磊磊在研讨会开幕致辞时表示,教育、文化、艺术资源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在民心相通方面做出独特的贡献。民心相通就是通过文化交流与合作,实现各个国家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借鉴、相互欣赏。文化交往是经济交往、外交交往、贸易交往、金融交往的先锋,是“一带一路”的灵魂。
南音,要美?要酷?
在泉州说文化遗产,南音是名列榜首的议题。这一以古泉州方言演唱、表演的方式,不仅属于泉州,而且从明朝起逐渐流传到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地区,至今仍在这些地区演出,为当地华人和艺术界所喜爱。新加坡的湘灵音乐社是南音表演团体,社长丁宏海说,他们的表演受到新加坡社会与媒体的关注与欣赏,他们要将南音打造成新加坡的文化品牌。“南管音律分外娇,声随游子处处飘,风风雨雨,潇潇寥寥……寂寞孤影夜,工工六工解无聊”。这是丁宏海父亲所作曲词,吐露海外游子对南音的情感依赖。
丝竹相和,执节者歌,每个音都要婉转几秒钟,箫、弦、板、琵琶,间有歌声如诉,表演者上下场交接时,要彼此行礼。观者就算不懂方言,也会被其中的内敛、有礼、优雅熏染。特别是有些生活阅历后,肯坐下来听1个小时,一定会体味到南音的“载道、净意、明心”。
但现代生活太急迫热闹,“酷”的追求覆盖了“美”。虽然文化工作者已看到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疗愈”价值,南音于2009年被联合国列为“非遗”,但事实是南音已几近“化石”。如何令其“活”在现代?无非是传承与创新。
对此,台北艺术大学林珀姬教授表示,传统和创新是两条路子,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就是要把传统传承下去,不要急于“嫁接”创新。“我们留下的东西,能否让后辈找回来时路”?林教授在研讨会上用声像展示台湾传承南音的现状:从南到北都有民间表演社团,台北艺术大学设立南管专业(台湾称南音为南管),在中小学成立南管乐团并举办比赛,台北孔庙举办研习班……台湾对南音的传承大多用的是民间之力。
丁宏海在研讨会上则开启了创新的想象,他在新加坡举办的南音演出,将旗袍、爵士乐队引入,观众看演出时有美食、香道、茶艺相伴,营造了“惊艳”的效果。丁宏海说,他们也有“正襟危坐”的演出,这种原汁原味的演出会选择在古厝、古戏台进行,再现“绕梁三日”的古意。让传统的归传统、创新的归创新,这是新加坡湘灵音乐社对“酷”与“美”的兼顾。
而南音的源头地泉州对南音的保护力量主要来自官方。2010年泉州师范学院成立南音学院,2013年福建省设立南音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中心,泉州市实施“南音记录工程”、排演南音新戏……泉州师范学院教授王珊在研讨会上提出,泉州仍保留南音的文化生态,民众的婚丧嫁娶、自娱自乐仍有南音相伴,将保护工程融入民间体系才能留住这一生态。
创新,要优?要阔?
既然是“遗产”,就说明已经脱离了原有的生态,远离了当代的日常。大部分来源于庶民生活的文化遗产,如果只成为学者研究、政府砸钱的对象,没有了大众的喜爱、需要,就如无源之水,会挽留不住地“蒸发”。文化遗产当然要保存,但也要创新,让其成为当代人的精神滋养。韩国学者柳在沂在研讨会上介绍了韩国将莎士比业戏剧用韩国传统歌剧呈现的尝试。南音文化传承中心创作了融合现代舞美、舞蹈的南音新剧《凤求凰》,越来越多的设计作品采用了文化遗产元素。在这方面,参加研讨会的几位大陆学者不约而同剖析了近30年前的原创舞剧《丝路花雨》的成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欧建平认为,《丝路花雨》的成功在于用舞剧的方式准确传递了敦煌文化之美,其中的《胡旋舞》、《霓裳羽衣舞》和已经成为经典的“三道弯儿”、“反弹琵琶”舞姿,完全取材于敦煌壁画,创作人员聚焦于文化的研究、还原、展示,以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将彼时的丝路时空“活化”,成就了至今仍在上演的精品。
反观近些年大制作的“丝路”舞剧,欧建平提出自己的思考与忧虑:集中全国最火的创作人员和演员,将飞天壁画按原比例搬上舞台,上百吨的舞美装置,将舞剧推高到“亿元俱乐部”时代。但是,在首演、得奖之后,各地演员散去,剧目就此停摆,本团演员没有得到演出机会和提高。上百吨的道具也很难受邀去演出,就算去演,也是“自己花钱给别人唱堂会”。舞不够景来凑,满台“尽带黄金甲”,这样的作品很“阔”,但不优,不优则速朽。
传播,要华?要实?
“一带一路”文化遗产是传播、融合的产物。既有“洛阳家家学胡乐”,也有“万国衣冠拜冕旒”。当下,遗产的保护、创新也离不开传播。在西方中心主义形成近百年后,中华文化如何再次随“一带一路”出发,是不少学者思考的议题。
爱深责切。台湾知名的南音研究学者吕锤宽说:“有人说反正老外听不懂,应付应付算了。如果老外给我们演奏莫扎特、巴赫的时候也是这种态度,我们会爱上交响乐吗?”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孙玉明有同样的批评:“有些翻译者连《红楼梦》的版本都没搞清楚,因为在国外学了几年外语就翻《红楼梦》,这样的译作能好吗?”
学者们指出,传播的出发点要爱文化、研究文化。福建师范大学教授袁勇麟以闽南民间艺术传播为例,提出他的观察与思考,提出现在面临传承人才断层、传播方式单一、海外传播效果不佳等问题。他建议先在文化的本乡本土培养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在原地挖掘传统文化新的功能,用民众的欣赏方式唤起他们的认同和“文化自觉”;其次,充分利用民间传播力量,政府组织的海外展演覆盖面是有限的,往往集中在当地的上层社会,应鼓励民间文艺团体受邀出国展演,规模也许不大,但如果符合当地的需求,便更能融入日常。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连辑在研讨会闭幕式上说,“一带一路”文化遗产是个大课题,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利用等难题,都在等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