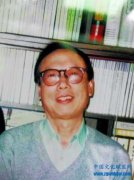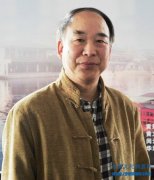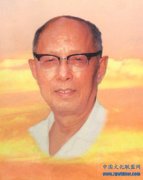——访著名作家汪兆骞散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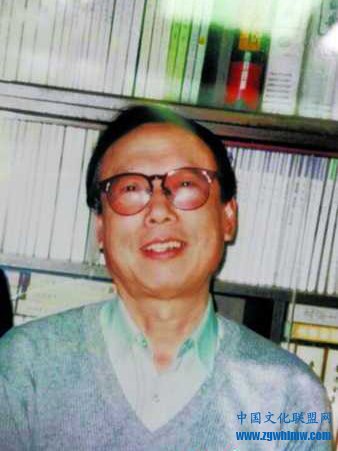
汪兆骞 笔名东方笑,1941年生,北京人,祖籍河北昌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64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任教师,1980年后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辑部副主任,《当代》副主编,编审。著有长篇小说《豪门云雨》《王府风雨》《伊王府奇案》等,评论集《侃爷王朔》,纪实文学集《张骞》《名人世界》《民国清流》,散文集《海神》《记忆飘逝》,评论《论通俗文学的审美价值》,与人合作电影、电视剧剧本《围猎》《四十八个日日夜夜》《消失的哨音》《南洋泪》等。
汪兆骞先生的新作《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在《清风文萃》杂志上连载,迄今已有数月之久,收获读者许多好评。盛夏七月,笔者返京,借由现代出版社社长、好友臧永清的安排,拜访了汪先生。
电话里汪老声音洪亮,干脆而利落:“到我书房来吧!”随后便把地址发了过来。笔者循址进入一个幽静整洁的小区,几幢高楼耸立,应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家属院。找对楼号,上楼叩门。
门开处,汪老笑脸相迎,温和而亲切。眼前的他中等个头,不胖不瘦,面色红润;身着汗衫短裤,腰板直挺,步履轻快,显得精神饱满,矍铄而干练;花白的头发,戴一副精致眼镜,一把折扇在手中轻摇时,透出些许已逾七旬老人的沧桑。
这确是一间书房,三面墙都是书柜,一些瓷器字画装点其中。当我们在面窗的两个沙发上坐定,随着汪老话匣子打开,我方知他的思维之敏捷,思想之前卫,以及记忆力之惊人;也才能想像到那数百万的文字是如何从他那睿智的大脑和矫健的笔下汩汩流出……

一
说到“笔”,汪老确实笔力矫健。何有此言呢?与汪老一个多小时的交谈给了我两个答案。
汪老说,来看他的朋友从不带烟酒,不带瓜果,常常是带一捆或几打HB型中华铅笔。汪老写作喜用笔,特别喜用铅笔。他说如今“笔耕不辍”的人已经不多了,作家们大都成了电脑的俘虏。据他所知坚持用笔写作的也就是还有刘恒、贾平凹等不多几个人了。而他,还是想要留下“手稿”在人间;再一个,只有用笔写作,他才能体会到文思泉涌的快感,而电脑写作总是会有思维上的“间离”效果,妨碍思绪的连贯和畅通。一束铅笔,一把剪刀,一瓶胶水,是他写作的必备工具,改写、剪贴应裕自如。他通常要每天早起散步,一是锻炼身体,二是构思。散步完毕,当天的写作内容已了然于胸,早饭后坐于桌前,3000字很快便跃然纸上了。
许多人惊异于汪老的写作之神速,且不提他之前出版的《往事流光》《春明门内客》《记忆飘逝》《紫塞烟云》《张骞》等作品,只说近两年,他何以能够在短短的时间里,接连出版了《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往事流光:见证文学的光荣年代》等逾百万字的著作呢?大家只看到了他的神速,却不知他有30多年的积累,他是厚积而薄发的学者型作家。我从这里悟出了汪老“笔力矫健”的第二个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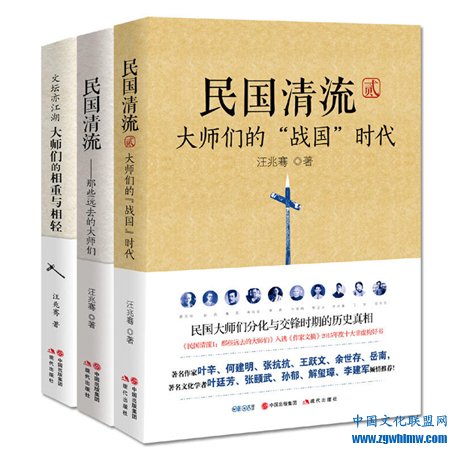
汪兆骞先生1964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任教师,自1980年起,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辑部副主任、编审,《当代》杂志副主编;他从1963年就开始发表作品,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他的这个简历里明眼人可以看出他作了30多年的编辑工作,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该有多少的阅读、多么深厚的积累呢?特别是“文革”10年里,当年的红卫兵小将们收缴了大量的文史资料,中央某部门一声令下,所有资料都放到人民出版社保存。那些资料之多、之珍贵甚至超过了北京图书馆的文史类馆藏。其中“五·四”时期的出版物分门别类,卷帙浩繁。这些资料在随后的那些年里成了汪兆骞的宝藏。他无事就往储藏室跑,抄录了大量原始资料,做了无数的卡片索引,在力有不逮的时候,他甚至委托他人代抄资料、做索引。长期而浩繁的积累,大量的一手资料,经过有30多年经验的老编辑专业而精明的梳理,缜密的研究和提炼,故纸堆里便跳出了金凤凰,透过历史的尘埃,向今天的读者显现出它迷人的身姿,那就是它历史的价值所在,是这些著作一经问世便引起巨大反响的原因所在。正是这一切,成就了如今笔力矫健的汪兆骞。
汪老说,他主编过许多丛书、文集,数十年的出版社经历沉淀了自然而然的编辑品格和休养,他有着自然而然的对历史的敬畏,对史料的尊重,看不惯现在的一些作家和出版物的东抄西抄,东拼西凑弄出来的东西。
我提到了20年前我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做史诗型系列巨片《大决战》《大进军》编辑的经历,深知对历史的敬畏何等重要,也深知收集史料的艰辛。汪老深以为然。
宁波海关聘汪兆骞、李炳银等评论家为该关文学顾问
二
汪兆骞先生生于1941年,今年已是75岁高龄。他的人生跨越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时期,经历了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他数十年身在京城文化圈,遭遇过数不清的文坛浩劫,也见惯了政坛上“你方唱罢我登台”的风云流转。他有幸能在一个长时间里深潜在历史的流光溢彩里,既有了作为一个作家对史料的占有,嘉惠于他后来的写作,也有了从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研究中逐渐形成的对历史新的认知,当他从历史深处蓦然回身时,便也改变和重构了他对当代社会多方面的认知。做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有对祖国、对人民深沉的爱,也有忧国忧民的炽热情怀。当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现象与他所坚守的原则、与他信奉的价值判断体系相悖谬时,他便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主张知识分子要勇于对现实“发声”。我理解他视所谓的“发声”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责任,为了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利益,他想要站在历史进步的一边。
汪老说,早在文革时就有领导让他入党,但被他拒绝了,他说,不入党也许对工作更有利,在党外也可以不给组织找麻烦。我理解,他是想更好地扮演一个社会批评者的角色,而一个开明正常、讲民主法治的社会这种角色是不可或缺的。
现在他经常被邀请到高校演讲,他总是要大胆地讲出一些也许不能见容于某些官僚的见解。他觉得,言之所及无愧于心,却有益于启迪他人的思考,着眼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就应该“发声”。
在北京师范大学为他的新书举办的《往事流光:见证文学的光荣年代》的主题讲座上,他跟大家分享自己对文学创作的见解时说:“文学反映人性的复杂性,复杂的人物形象才是一个完整的文学形象。然而,我们的一些作家往往在作品中造神,形成了苍白的人物。”“好的作家责任重大,他们担负了独特的历史使命。”他举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她是在用自己的力量呈现给世界真相”。他说:“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用自己的文学作品挖掘国人身上的人性与野性,塑造出一个个丰富立体的人物形象。如果说文学是人学的话,考察文学作品的好坏就是要考察作者挖掘人性的深度与广度。”
“努力把真相呈现给世界,让历史不再只有一种声音、一种可能并不接近真相的声音!”我注视着汪老炯炯有神的双眼,听着他掷地有声的话语,恍然感到,这哪是一个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分明有几分热血青年的感觉!他象是从百年前“五·四”运动的历史洪流中走来,昂然肩负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责任担当!我也赫然明了,百万字的《民国清流》写尽了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彷徨和呐喊,他们中的许多人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是民国初年纷嚣社会中的一泓清流。而这百万字的作者,随着笔下汩汩流出的文字,已被那泓清流感染和裹挟,已心甘情愿要承继那泓清流的精神血脉。他期望那清流历经百年坎坷,仍能不绝如缕,有朝一日终能汇成滔滔洪流,创造历史,并为历史所铭记。
三
一个多小时的谈话间有一个小插曲:我被汪老的情绪所感染,翻开带给他的一本《清风文萃》杂志,其中有《任志强回忆录:野心优雅》的连载,那是本刊在任志强因质疑“媒体姓党”而被宁左勿右的某些官员所“修理”后开始发表的。
汪老惊异地抬头,投过赞许的目光。他倏然起身走进另一房间,稍顷,拿了一本书返回。那本书是他刚出版不久的《往事流光:见证文学的光荣年代》。他说,中国文坛的所有作家都在他的关注之内,而这本《往事流光:见证文学的光荣年代》是他写其中一些大家的评论、散文集。我深知汪老所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编辑部在中国文坛的巨大影响力,多少作家是在他们的慧眼识珠和扶持培养下才得以成长和成名。他对他笔下的那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有着入木三分的了解,其间的故事也一定会意趣盎然的。《清风》杂志的读者若能有幸读到这些佳作,该会是多么地开心啊。
思绪还在我大脑里盘桓,汪老已经开口:“你若愿意,这本书上的所有文章都可为你所用!”我大喜过望,连声致谢。
汪老找来笔,在书的扉页上签名,并小心地盖上了他的印章,并让我拍照,合影留念。
他说:“你在海外办中文杂志,传播中华文化,我理应支持帮助。”他问及杂志多少钱一本出售,我告诉他是免费发放,只是靠广告维持生存。他叹说不易,允诺有需要时尽管张口。
时已近午,我起身告辞。汪老送至门口,有力地握手。——《中外名流》第17期访谈·纪实
外面晴空朗日。
我怀着崇敬回望那幢建筑,它高大、坚实、挺拔地耸立在那里。我知道,这里是知识分子聚集的群落。
愿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它般顶天立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