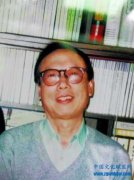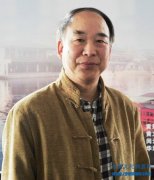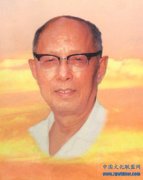飞机到达泸州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了,走出满眼充斥着各类白酒广告的机场大厅,见到等候在外面的泸州市文联的同志,我们一路上的劳顿立刻便被他们的热情化解得无影无踪了。在主人的陪同下,我们来自北京的一行8人上了一辆中巴车。车子向泸州郊外驶去,大约跑了一个多小时的路,驶进了一个小镇。忽然,一阵酒香从车窗外飘了进来。我往窗外一看,原来道路两边酒肆林立,我们车停靠的道边便有一家四门大开的小酒铺。主人告诉我们,这到的地方就是泸州辖区的二郎镇,镇上还有众多的酒厂,著名的郎酒就出自这里。
早就听说泸州是座酒城,泸州老窖、郎酒等许多名牌白酒都出自泸州,更不用说数不胜数的那些没名气的小酒厂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泸州酒的氛围这么浓,尤其是酒厂或酒肆周围的空气都带着酒的味道。然而,泸州绝不仅仅因酒闻名,除了酒,泸州还有大量的红色文物。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曾驻扎在泸州古蔺县太平古镇,在那里留下了红军中央机关的众多旧址。而在镇郊外的赤水河边还有红军四渡赤水战役的一处渡口——太平渡渡口。

杜希贤鹰作品《高远图》
向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捐赠作品,并到红色景点参观采风,才是我们到达泸州的真正目的。作为媒体记者,我有幸受邀参加此次活动。我们一行人中,除了泸州当地文联和北京海淀区文联的几名领导外,主要成员是来自北京的五位书画家,他们是著名国画家、北京海淀区美协主席杜希贤,著名画家白崇然,著名书法家、海淀区书协主席周持,著名书法家、中国书协理事龙开胜以及书法家、作家张瑞田。对于后四位书画家,我也是在北京机场登机前才见到他们本人的,而对于他们中最年长的杜希贤主席我却并不陌生。此前我因为采访他,以及在一些书画活动上和他相识并结交。我事先并不知道他会参加此次活动,直到我在机场看到人员名单上有他时,才知道能和他一道去四川。因为我们有快一年没有见面了,所以,我很期待见到他!
当杜主席微笑着并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大家起身迎了上去,纷纷上前和他握手寒暄。“杜主席,能和您出差,太好了!”我双手紧握着他的手说道。“我看到名单上有你参加。这回我们可是同路了。”杜主席笑着说。“是啊!路上要是您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尽管吩咐啊,杜主席。”我说话的同时,扫了一眼杜主席的身旁,发现他只带了一个不大的布料挎包,再没有别的大件行李。“杜主席,您的行李呢?”我问道。“就这一个。”杜主席说着,随手拍了拍他背着的挎包。毕竟出差时间也有三四天,但他却只带了这么个不算大的挎包,着实让我感到有点惊讶,但转念一想,倒也理解,他的确不会像一般人那样带上好多随身用品,尤其是带太多的服装去远行,因为他好像不是很讲究穿戴,就连服装的色调也总是像他这个人似的有点低调,喜欢穿着一身深色的衣服。他给我的印象总是很平和,文雅而谦恭,一种学者的气质。虽然他看上去头发灰白得挺多,但宽大的前额,少有皱纹的脸颊,让他看上去真不像一个接近耄耋之年的老人。

杜希贤鹰作品《雄风》
杜老师是山西人,1937年生。他曾在上世纪50年代就读于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后称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1960年大学毕业后,由于他人物画写实能力强,被留校任教。后来因艺术学院被国家撤销,他被转至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直到退休前他一直在该校担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退休后,他并不清闲,社会职务很多,担任着北京海淀区美术家协会主席,此外他还是中央文史馆书画院研究员。因为他平日忙碌,所以有两三次我想去拜访他,都没能如愿。
我们到达二郎镇时天色已晚,主人安排我们一行人在镇上的一家干净整洁的小旅馆里下榻。随后,在镇政府食堂招待我们吃了一顿农家饭,并让我们品尝了当地的名酒——郎酒。酒是很有名,打开后酒香四溢,但喝过之后也没有留给我太深的印象。只是我发现杜主席并不能喝酒,但不管谁来给他敬酒,他也不退让,并且稍稍地喝上一点……
翌日,早饭过后,我们大家又上了来时的那辆中巴车。车子驶离旅馆,在晨曦中开上了公路,直奔古蔺县太平渡渡口,前往参观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码头旧址和纪念碑。
从二郎镇到太平渡渡口虽然只有40多公里的车程,但多数时候汽车是行驶在蜿蜒的盘山路上。一路上,坐在车前面座位上的我不时地被沿途的风景深深地吸引着。
此时正值6月的多雨季节,山区里空气湿度很大,山峦起伏,云雾缭绕,真好似一幅巨大的水墨画。不知什么时候,天空开始下起了小雨。路边的草木被雨水打湿后显得更加葱翠,盘山路下面是一条深达百米的河谷,中间缓缓流淌着一条浑浊发红的大河,据说那就是闻名的赤水河。在蒙蒙细雨中,远处的山峦时隐时现,别有情趣……

2015年6月作者王玉君与杜希贤(左)在四川泸
州太平渡渡口红军四渡赤水纪念碑前合影
然而,同车的其他人好像并不像我这样沉醉于外边的景致。坐在车后面的几位书画家们一路上只顾说笑聊天,好像全然没有看到外边的风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坐在车中间首长专座上的杜主席和大家聊得兴致很高。聊的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大概都是关于齐白石、徐悲鸿、黄宾虹等大画家的故事。因为我想多看看外边的风景,自然也就不多插话,但对他们聊的这些内容我有时也注意听听。
渐渐地雨停了,我们的车子也开到了太平镇渡口,这里有当年红军四渡赤水时的一处码头旧址——老鹰石。从停车场到老鹰石渡口,我们需要徒步走上六七百米的土路,路面有些湿滑。我想这对上了年纪的老人可能不太好走。于是,我便走在杜主席身边,以便需要时能搀扶他一下。
“杜主席,小心啊。路不好走,要我扶您走吧?”我关切地问。
“谢谢你。不用的,小王。我没事儿。”杜主席和蔼地说。
因为看他走的脚步很稳,我也就放心了。
在赤水河边的老鹰石渡口铺着地砖的平地上,一个高达十多米的纪念碑矗立着,石碑正面从上到下镌刻着“中国工农红军太平渡渡口”这几个字。导游告诉我们,红军长征期间,为跳出敌人包围圈,毛泽东出奇制胜,成功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成为古今战争史上的经典之作……站在纪念碑旁边的一些人在聊天,而我却看到杜主席一个人正在眺望赤水河的对岸,似乎陷入了沉思。于是,我走到他跟前,想趁机采访他一下,听听他此时此地有什么感想。听我要采访,杜主席转过头看着我,思索了片刻后,说道:“要是当年没有毛主席指挥红军,革命肯定失败了,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有的人总想诋毁他老人家,那是绝对错误的,无论如何,我们不要忘记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啊!”他讲话时声调不高,但语重心长,掷地有声。
参观了太平渡码头和红军四渡赤水纪念碑,我们又上了车,没开多远,便到了太平古镇。下了车,我们走到一个很宽阔的广场上,远远地便看到广场一头建有一座颇有民族特色的灰白色房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上午10时许,著名画家白崇然捐赠给红军四渡赤水太平镇陈列馆国画长卷《长征万里图》仪式在陈列馆门前广场上隆重举行。泸州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古蔺县有关领导莅临活动现场并讲话。画卷长达36米,以青绿山水的形式,艺术地描绘了红军走过的长征之路。当画卷被十多个戴着白手套的工作人员在广场上缓缓打开时,在场观众无不啧啧称赞。对于海淀美协副主席白崇然捐赠的善举,杜主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白崇然先生为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捐赠书画具有深远的意义。他还告诉我说,明天我们还要再和当地书画家搞笔会,把作品全部捐赠给这个红军四渡赤水陈列馆。
仪式结束后,我们在主人的陪同下,走进陈列馆,听讲解员介绍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参观红军留下的一件件革命文物,感受当年革命斗争的峥嵘岁月。在一幅红军写的标语文物旁,杜主席停下脚步,颇有感慨地说,“你看,这标语上的毛笔字写得多好啊。当年革命队伍里有许多文化人,他们投身革命,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参观完陈列馆,我们又跟随导游徒步来到纪念馆附近的太平古镇,继续参观那里的红军革命遗址。
古镇上的房屋多是木质阁楼或小屋,据说是清代民居,它们多依地形而建,参观时经常需要登爬阁楼,或是拾级而上。杜主席一直饶有兴趣地走在我们中间,有时他看得非常认真,仔细端详那些革命文物……
在泸州,我们还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为红军四渡赤水陈列馆现场创作一批书画作品。到达泸州的第三天下午,我们在泸州市文联的安排下,乘车来到古蔺县城郊的一处古色古香的茶楼。在这里,来自北京的五位书画家同当地几名书法家开展了一次有意义的笔会活动,他们将现场创作的作品全部捐赠给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
笔会在茶楼的后院举办。这是一个面积不过百来平米的小院,小院的一侧是山坡,院子里花木苍翠。院子中摆着五张宽大的桌案,每张桌案上都铺好了白色的毡布。因为院子里的桌案少,来的人多,于是杜希贤和白崇然二人决定发扬风格,两人将共用一张桌案,合作创作一幅作品。初步商议画面布局后,杜主席首先开笔。只见他拿起一支木炭条,在桌上的一大张雪白的宣纸前凝视片刻后,弯下身来,在纸上简单地勾画出一只雄鹰的轮廓。待轮廓确定后,杜主席又拿起了一支不大的毛笔,把笔毫先在一碗清水里润了一下,然后伸到旁边的盘子里沾上墨汁,并细心地调好笔锋,开始下笔作画。此时,毛笔在他的手上时快时慢地移动着,一阵清风袭来,散发出淡淡的墨香。不大一会儿,一只雄鹰的眼睛、弯曲锋利的喙,乃至鹰的头部造型都在他的笔下勾勒出来了……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杜主席画的鹰翅膀上的羽毛。他用毛笔的笔肚,通过调整水分,在纸上点着长短不一、墨色分明的墨点,墨点之间相互交融,自然地显出水印,便把鹰翅膀上的羽毛层次和质感巧妙地表现出来,让人不能不感叹艺术家用笔的神妙!本以为杜主席画完一只鹰就结束了,让人没想到的是,他在画好的雄鹰旁边又画了一只不同姿态、栩栩如生的雄鹰!这让我很感慨,我曾接触过有些书画家,他们对于捐赠作品的创作好像不是太上心,能偷懒的地方就不多画一笔,而杜主席却不是这样!待他收笔后,白崇然老师搦管染墨,提笔挥毫。只见白老师在画好的两只雄鹰旁边画上一棵苍松。不同于杜主席的慢笔勾描点染,白老师完全是采用大写意的笔法,尽情挥洒,不长时间他便画好了一棵枝叶茂盛的苍松。两位画家将不同的题材呈现在同一幅作品上,而又做到了画面十分协调、统一,令在场观者赞叹不已。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很多书画家已经创作完了,有的桌案已经没有人用了,院子里的地面上铺满了他们创作的一幅幅尚未干透,散发着墨香的书画作品。正当我一幅一幅地观赏着这些作品时,一位陪同我们来的当地领导走过来问我是不是也能写会画?可不可也留下个墨宝?我听后很兴奋,便跟他说,我会画啊,但恐怕笔会要结束了吧?不曾想,那位领导却告诉我,至少还要等三四十分钟才结束,你要是觉得时间够用,就在这也留幅作品吧。我想,这么短的时间让我画幅大的山水画是来不及了,但我还是也可以画棵松树啊。用松树象征着红军战士的精神,捐赠给陈列馆很合适。于是,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并裁剪下一块大约三平尺的长方型宣纸。也就二十来分钟的时间,我便用大写意的手法画出了一棵长在山崖峭壁上的苍松,并且还画上了远山、瀑布。就在我快要画完时,我看见杜主席从屋里出来。我赶忙放下手里的毛笔,朝他迎了过去。“杜主席,请您过来看看我画的画好吗?”“好啊!”听到我的请求,杜主席一边说着,一边跟我走到我的画作前。
“你松树画得还不错,尤其是树干的用笔挺好。不过,远处的山和瀑布画得墨色有些过重了,如果画得再淡些,会更好看。”杜主席的话,让我很是感动,我觉得他是在鼓励我这个晚辈。我知道我在匆忙之间完成的这张画还不是特别完美,但没想到的是,他不仅没有打击我的积极性,还给了我这样好的评价!更没想到的是,我的那幅拙作也被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收藏了,并且还给了我一个大红封面的荣誉证书。
在泸州的两三天里,我一有机会便和杜主席聊天,请教。他送了我一本他的国画作品集,我翻开发现,绝大部分作品都是他画的雄鹰,他的作品里有各种姿态的鹰,有空中飞的,有在松柏枝头或悬崖巨石上的,有单只的鹰,也有两个或几个鹰在一起的。我发现,其实他不仅是鹰画得好,那些雄鹰栖息的古柏更是被他画得逼真,他把古柏树皮的质感用毛笔表现得惟妙惟肖。再往后翻开他的作品集,我发现里面还有几张人物画,是杜主席早年的作品。这让我感到他其实不只是能画鹰,人物画也很有实力。从他画的《老农民》《女青年》等人物画便可以看出,杜主席的人物造型的确是功底深厚,笔墨风格颇似大师蒋兆和。
谈起他年轻时的故事,杜主席还告诉我,早年他在首都师范大学任教期间就曾跟同是做学校教员的白雪石友情笃深,那时,白雪石还没有出名,画也不太好卖,家里夫人有病,孩子又多,生活很困难,于是当时作为担任教研室生活秘书的杜主席对白雪石就格外关照,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杜主席还告诉我,十多年前,他就开始为北京一家老年大学义务教授人物画,直到现在还在教。其间他因搬家路远等原因几次想要退出,但都始终没能实现。原因是那些老同志就是喜欢让杜主席教他们人物画,尽管杜主席也曾推荐过别的名画家去替他上课,但那些老同志就是不接受,认为只有杜主席教他们的人物画才是正路。
杜主席的人物画有功夫,他却以画鹰出了名。有评论家说,杜希贤在画鹰时做到了笔墨与鹰的形体质感有机结合。其用笔沉稳,笔墨圆润厚重,很好地把墨色的变化和干湿浓淡结合起来,形成枯焦滋润之对比,构成丰富细腻的笔墨妙趣。
我曾问杜主席为什么那么喜欢画鹰,他说他崇尚鹰的品格,另外,就是因为很多人都喜欢他画的鹰。“鹰走天路,取高为驿。极目四野,气贯奥汉”——这是鹰的品格,或许也是杜主席喜欢画鹰的缘由。我想,从他把画鹰作为主要的绘画题材来看,在他温和谦恭的外表下,一定潜藏着和鹰一样的品格,和鹰一样不畏风雨雷电的志向。在他的骨子里必然有一种像雄鹰那样展翅高飞的豪气雄风。正如他说的那样,他画鹰,就是寄情于鹰,借鹰言志,以画鹰来赞美一种崇高的精神,表达自己的心声。正是因为这一点,我觉得他和白崇然合作的那幅“松鹰图”,捐赠给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是再合适不过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鹰的那种不屈不挠、搏击千里的精神或许就是我们今天应该提倡的长征精神。
时光荏苒,转眼间我们离开泸州差不多有一年了。说实话,泸州的酒香并没有让我产生留恋回味的感觉,但杜主席和白老师完成的那幅水墨松鹰图,以及书画家们留在酒城的墨香至今仍让我深深地陶醉……——《中外名流》第16期访谈·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