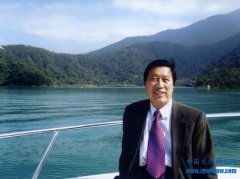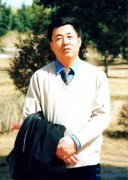崔道怡 1934生,辽宁铁岭人。中共党员。1951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历任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小说组长、编辑部副主任、副主编、常务副主编,编审。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8年曾获全国文学期刊优秀编辑奖,1996年曾被评为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被誉为“天下第一编辑”,有伯乐精神。
主要作品《创作技巧谈》《小说创作入门》《小说创作十二讲》,儿童文学《队员的道路》,短篇小说《关于一个鸡蛋的“讲用”》,中篇小说《未名秋雨》,主持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新中国五十年短篇小说精品》丛书等。
崔道怡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1956年,22岁的崔道怡分配到《人民文学》杂志当小说编辑。当时,恰逢《人民文学》杂志的繁荣期,王蒙写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望着血气方刚的崔道怡,《人民文学》杂志社的人开玩笑说咱们编辑部也来了个年轻人。
刚一上任,他就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李国文。李国文当时是铁路文工团的业余作者,一口气写了六个短篇小说寄给了《人民文学》。崔道怡觉得小说写得很精彩,就给李国文写信热情肯定了他的作品,并约他来编辑部见面。李国文接到信激动万分,马不停蹄赶到《人民文学》杂志。崔道怡对他说:“这六篇小说写得都不错,但《改选》写得最好。你修改一下,我先发这篇,往后再慢慢发那些。”
李国文按照崔道怡提出的意见修改了小说,《改选》在1957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头条发表了。从此,文坛上升起了一颗新星。直到现在,李国文仍然保存着崔道怡写给他的第一封信。崔道怡开玩笑说:“国文,把我的信还给我吧,怎么说我也是原创啊。”
李国文说:“我复印一份给你,原件我要永远珍藏。你知道一个名牌杂志的大编辑给一个小小的业余作者写信意味着什么,你是我文学上的摆渡人啊!”
1962年,党的文艺政策调整,崔道怡又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一个叫汪曾祺的作者。他的小说《羊舍一夕——四个孩子和一个晚上》,不仅题目充满诗意,而且内容很有味道。他及时把小说上报主编,编发时还提出请画家黄永玉为之插图。很快,汪曾祺的这篇小说就刊登在《人民文学》杂志。18年后,汪曾祺又写出小说《受戒》,崔道怡激动万分,称之为可以传世的精品。由于种种原因,这篇作品未能获奖,崔道怡便将《受戒》收进自己编辑的“获奖以外佳作选本”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鼓励汪曾祺。汪曾祺不负众望,很快又写出了佳作《大淖记事》,荣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有人认为这篇作品结构不完美,崔道怡却觉得结构别出心裁。事隔多年,汪曾祺深有感触地说:“我的作品能得到老崔的欣赏,我就像喝了瓶老酒似地从心里往外舒坦。”
60年代初期,一封来自内蒙古的来稿信引起了崔道怡的兴趣,作者叫玛拉沁夫,崔道怡觉得小说的生活气息浓郁,但艺术上还欠火候,就给作者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意见,希望他能修改。玛拉沁夫说:“崔编辑,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修改,我在呼和浩特熟人太多,根本静不下心来。干脆咱俩躲到包头,您指导我改好吗?”
那时候的编辑就是这么敬业,为了一篇好稿可以踏破铁鞋。崔道怡和玛拉沁夫住进了包头宾馆一个套间,玛拉沁夫住在里屋,崔道怡住在外屋。有崔道怡在身边,玛拉沁夫觉得有了主心骨。他写一段,崔道怡看一段,提一段意见,两人边讨论边研究如何改写,桌子上散落着雪片般的稿纸,两个年轻人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在崔道怡的帮助下,玛拉沁夫很快就修改好小说《腾格里日出》,刊登在1964年第10期《人民文学》的头条。
“文革”期间,文坛百花凋零,《人民文学》停刊了,编辑们各奔东西。1975年,李季主编把原来《人民文学》的编辑都调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筹备《人民文学》复刊。崔道怡从《天津文学》杂志发现有个叫蒋子龙的人写东西不错,就约他到出版社见面。蒋子龙高高兴兴来到出版社,崔道怡得知他是天津重型机械厂的工人,就建议他写点最熟悉的工厂生活。那年头名牌编辑接见业余作者是件很荣耀的事情,受到鼓舞的蒋子龙一鼓作气写出了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描写一个工厂的中层干部大胆抓生产的事。崔道怡鼎力相助,这篇小说于1976年1月刊登在《人民文学》复刊号上。那时候“四人帮”还在台上,帽子棒子满天飞,在黑白混淆的日子里,这篇小说遭到批判,说是应合了右倾翻案风。作为小说组副组长和责任编辑的崔道怡挺身而出,替蒋子龙抵挡风雨。粉碎“四人帮”后,蒋子龙欢欣鼓舞,写出了《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一批重量级的小说,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著名作家。
崔道怡广泛浏览各地的文学报刊,一个叫刘心武的新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觉得刘心武的文章中有一种特立独行的东西,便写信向他约稿。刘心武当时是北京十三中学的老师,接到《人民文学》编辑的来信很受鼓舞,他把自己写的小说《班主任》寄给崔道怡。崔道怡看后非常激动,立刻给刘心武回信说:“稿子写得很好,我已提交给主编审阅。”
刘心武接到崔道怡的信心潮起伏,因为稿子才寄走一个礼拜就收到了编辑肯定的来信!但没想到小说在编辑部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这篇作品太危险,当时中央文件还没有正式否定“文革”,这篇小说会不会捅娄子?崔道怡据理力争,在主编与几位同行的支持下,《班主任》于1977年夏天刊登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立刻在全国掀起巨大反响。那时候的《人民文学》杂志发行量达180万份,在读者中有很高的威望。那时候的中国人对文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人们喜欢从文学作品中看政治动向。《人民文学》独领风骚,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和刘心武的《班主任》振聋发聩,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启蒙作用。从《班主任》之后,《人民文学》杂志发起建立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奖,极大地促进、繁荣了新时期的文学创作。
崔道怡有着42年的编辑经验,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极高,很少看走眼。所以很多著名作家都把崔道怡对自己作品的鉴赏,视为一种重要评价。王蒙曾经在一篇《关于<夜的眼>》的文章中写道:
“当时没有几个大家注意它,最好的也不过说你再试着创新吧。只有《人民文学》的崔道怡对之赞不绝口。他坚持把它收到建国30年小说选里去了。当时与中国关系并未正常化的苏联很快把它译成俄语,选到他们的《外国文学》杂志里。八十年代美中第一次作家对谈时,美国人带来了他们的一个中国当代文学译本,收了这篇小说,对它作了好的评价……”
崔道怡老师对作家的关爱令人感动,2005年,我出版了全景式反映我国西气东输工程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动脉》,这部作品是中国作家协会的重点扶持作品,一天,我突然在《文艺报》上看到崔道怡老师对拙作的评论《气壮山河的史诗》,心头一阵热乎乎的。过了几天,中国作协召开《中国动脉》研讨会,白描对我说:“孙晶岩,一会儿你要认真听听崔道怡的发言,他的发言很有水平。”
过了片刻,崔道怡老师对拙作做了热情洋溢的点评,我的眼眶变得湿漉漉的。搞报告文学难啊,尤其是花几年时间走几万里路在生活一线打磨出来的72万字的作品,其中甘苦,唯有自知。我感受到他对作家的真挚关爱和殷切期望,暗下决心,一定努力创作,不辜负他的期望。
后来,我一鼓作气接连创作了七部长篇报告文学《五环旗下的中国》《女监档案》《震不垮的川娃子》《珍藏世博》《中国看守所调查》《西望胡杨》《北平硝烟》,每写一部他就力挺一部。他问我为什么有这么旺盛的创作激情,我说诚惶诚恐,不敢懈怠,为了报答关爱我的老师和朋友,我必须认真创作。
我应北京市文联之邀四下和田,与援疆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采访人数达200余人,创作了59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西望胡杨》。该书出版以来,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西望胡杨》举办研讨会,崔道怡老师的开场白,更以几个具体数字引得大家一片笑声。他说,这是一部厚重的书:我称了称,书重达840克,光目录就有11页,在当前的形势下,该书的出版可谓恰逢时宜。该书记录了北京援疆干部隐秘的内心世界,为辉煌的援建岁月留下了传记,这是作者血汗的积累,也是援疆人的群英谱、功劳簿,是一部展现新疆和田发展变迁的史诗。
长篇报告文学《北平硝烟》杀青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文化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文学》《十月》《中国作家》等报刊杂志予以刊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做了长篇联播,社会反响强烈。崔道怡老师对我说一定要好好拜读,因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写的这段历史是他亲身经历过的,读起来很亲切。
崔道怡一生甘为绿叶,不愿抛头露面,可他却得到了大家发自内心的尊重。正如李国文所说:“一些赫赫有名的作者,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都和崔道怡的发现分不开的。”——《中外名流》第16期人物·探索